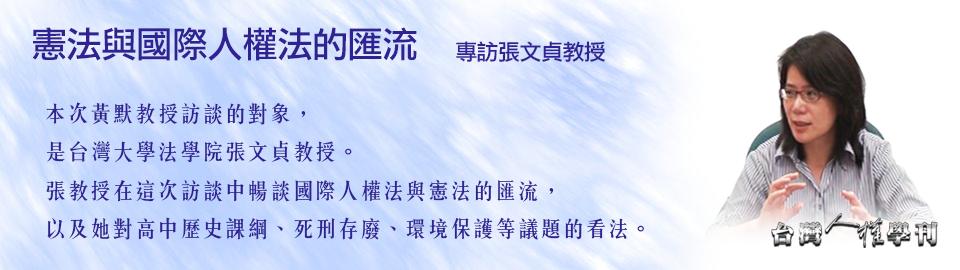
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流|專訪張文貞教授|人權群像第一季第五集
張文貞教授
本次黃默教授訪談的對象是台灣大學法學院張文貞教授。張教授在這次訪談中暢談國際人權法與憲法的匯流,以及她對高中歷史課綱、死刑存廢、環境保護等議題的看法。
專訪張文貞教授(一)
黃:大家好,我是黃默,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台灣大學法學院張文貞教授來做訪談。張文貞教授是我們非常出名的憲法跟人權國際法的學者,過去幾年在短短幾年內發表非常多的文章,得到非常好評,在我們人權學刊第一期、第二期,張文貞教授都發表了非常有水準的、非常有見地的文章。第一期她談的是有關環境人權法的、環境法律的主張。第一卷第二期她談的是一般性意見做為國際人權公約的權威解釋。那時候在台灣,那時候是剛剛通過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那有不少的討論就是說,這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通過以後是產生什麼效力,什麼解釋,那是不是一般性意見也應該做為解釋。後來,在稍後,張文貞教授也對這個我們在撰寫國家人權報告的時候,我們是得到⋯⋯還是法務部做為這個人權諮詢委員會的秘書處,這樣一個事情寫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也引起很多注意跟討論。張文貞教授的看法就是說,這並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規劃,可能引起秘書處、可能受到法務部的影響,不能比較公正客觀地執行他的工作,我也很同意張教授的看法。同時,當時可能開始的時候,大家對這問題瞭解比較少一些,現在這幾年下來看來大家對這問題就比較有一個進一步的瞭解,那是有一個內在的矛盾。在當時,即使在現在,就是說假如不是法務部來擔任幕僚工作,那是什麼機構能擔任幕僚的工作?待會兒我們再請張文貞教授對這個問題也再看看、再把她的想法,我們再來請教她的想法。我想我的訪問分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我們希望張教授能談談她的研究教學,尤其有關憲法跟國際人權法她受教育的背景。第二部份談到參加公共事務的活動,她對台灣的人權活動或者政府推動人權政策有什麼樣的評價,能不能先請張教授談談妳的背景,妳受的教育、妳在學術上、研究上的關懷?
張:謝謝黃默老師一開始的介紹,對於很多我這幾年的一些努力的美言,我實在不敢當,我倒是很想要談談與憲法或國際人權法的接觸。我是1988年到1992年這四年在台大法律系,畢業了之後,1992年到1995年在台大的法律研究所,是公法組。坦白說,在我大學四年的過程當中,除了必修兩學分的國際公法之外,我對國際法其實沒有太多接觸,更不用講國際人權法,當時對於人權的理解,都是在台灣民主轉型的脈絡下,對於政治啊那些社會議題的關心,那樣的一個人權脈絡。我真正第一次接觸到國際人權體系,也是一個因緣際會,我剛剛說我是1992年到1995年三年在台大法研所唸公法組,1993年我印象很深刻,那年陳隆志教授因為黑名單解禁,回到台灣。然後,當時其實我還不太知道陳隆志教授,也是因為他回來台大,台大整個對他的歡迎,我才知道說原來陳隆志教授,是早年台大法律系很優秀的畢業生,那出國到了耶魯大學唸書,專長國際公法,也因為他在國際公法領域一些也許對台灣國際法的論述,使得他變成黑名單,長期不能回來。所以黑名單解禁之後,1993年陳隆志教授回來台大,跟已經過世的蘇俊雄大法官合開了一門課,叫做「國際人權與世界秩序專題研究」,我就修了那們課。坦白說那門課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國際人權世界秩序、聯合國體系,國際人權公約,好在有那門課,除了那樣一個初體驗之外,我其實在整個台灣法學界,憲法、公法、實證法的脈絡下,其實很少提到國際法、國際人權法。
黃:我想這個對後來對研究並沒有什麼傷害。我現在又回去讀John Nash的The Beautiful Mind,他從來沒修過經濟學,他只在卡內基大學大學部修了一門經濟學導論,這並沒有傷害到他後來的一個寫他的畢業論文,得到諾貝爾經濟獎。你看這情形不難理解。
張:就是一些機緣。所以⋯⋯但那個理解我覺得還是重要的。所以1995年畢業,在台灣工作兩年,1997年我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到那邊的時候,就開始發現,哇,有非常多的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那,後來成為耶魯法學院的Harold Koh,他後來是我博士論文的committee member,當時他也上國際人權法,transnational legal process,很多很豐富。所以讓我至少不像我一般這年代台灣法律人,到了出國之後接觸到國際法、國際人權,不會害怕,也知道自己其實知道的很少,所以出國唸書的時候,就比較願意去接觸。還有一個,除了這個契機之外,我也覺得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1997~2001年,那後剛好1998關於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討論,美國的很多立場。所以我到美國,先有這個體會。我到美國唸書的期間,我自己後來在學術研究上,我把它叫做在整個 憲法跟國際人權法匯流的一段時間,其實美國也是一個向來比較重視它自己內國憲法,比較不重視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但是在上個世紀的世紀末,新的千禧年開始,即便在美國的法學院也已經看到很多談憲法的人權,會去談很多國際人權發展的趨勢。那甚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好幾個引用國際人權公約的判決開始出現。那當然法學院就出現很多辯論,應該不應該,但是那個辯論越多越反而促成,不管贊成或反對,憲法或國際人權法的那個匯流討論交織,就越來越清楚。
黃:你說得很對,美國傳統是對國際法並不那麼重視。美國法學界對憲法把它看作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也沒錯,但是到了你說的那個時候開始,就開始受到國際法的衝擊。我記得在早幾年,已經很多年了,有一個力量不是來自於法學院、法學界,是來自民間的力量,假如我沒錯,福特基金會協助還是補助好些亞非裔的草根的 民間組織,來探討、來討論美國社會為什麼應該把國際人權法帶到美國來。我想一個程度-當然我瞭解很少,一個程度他們的說法是,亞非的這些族群,受到憲法的保障比較少一些。在他們看來,假如引進國際人權法,對他們是有幫忙的,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張:這也是一個面向。那另一個面向我感覺是這個,對從歐洲歐盟在上個世紀它崛起開始,歐盟的發展,歐盟的人權公約,歐洲人權法院,越來越發揮它的功能,然後亞洲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使得很多 的規範上的對話,開始必須要跨國或跨洲。那美國,美國不能只跟德國談,美國必須要跟歐盟、歐洲人權公約相關的會員國談的時候,那個層級勢必要拉到所謂國際人權公約、區域人權公約的層次,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有影響。當然剛才黃老師講的是說美國它是個移民國家,所以新來的人他在還不能受到憲法保障的時候,他要怎麼樣去尋求他人權的論述。還有一個是2001年就是我回來美國,很快的911事件,一個恐怖的攻擊,後來反恐的這個,它是一個國際性的事件,所以它會引發國際人權、在國際規範的討論,尤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後來美國政府因應反恐,所謂的愛國者法,裡頭很多違反人權的措施,就用到了,比如說Four Geneva Conventions,四個日內瓦公約等等,所以,這也是一些契機的發展。
黃:沒有錯,我看在當前談人權保障,不只限於憲法,看來是我的說法就是說,應該還是很容易把國際人權法帶到這個討論。但這裡有一個比較奇特的情況,在我們這裡,在台灣有不少憲法學者都對這很遲疑。我多年來都不怎麼瞭解,他們為什麼那麼遲疑,他們堅持說我們只談憲法,我們談人權自由的保障,我們不需要去關照、關注國際人權法。妳對這問題怎麼看?
張:我覺得不意外,就是說我剛剛談,其實憲法跟國際人權法的匯流,在整個國際趨勢上,也是1990年代末期,到這個世紀才開始,我們剛剛談了幾個,歐洲的崛起,歐洲人權法院發揮功能,然後就911事件等等,它改變了過去一個典範,過去的典範其實是憲法是內國法,國際人權法是國際法,國際法跟內國法是絕對一個截然二分的領域。做憲法研究教學的學者他會認為說,這兩個是不相關的事情,他也不會有。所以我能夠理解我的,我剛剛講這樣的背景,我剛好在美國法學院,也很少見的國際法跟國際人權法匯流的那個moment,那個momentum,我剛好在那裡學習,所以我很自然的接受了,這必然是如此,它必然的對話。那可是等我回國之後,回來再看到原來台灣、在台灣受教育,受到內國法跟國際法二元區分,這是兩個井水不犯河水的領域,你能夠理解他為什麼這樣想。
黃:這是比較不幸的,多年來在威權體制之下,我們對憲法並沒有那麼多的研究跟探討,在這樣的情況我想尤其需要去帶進國際人權法,來補足我們背景的不足。但是如果我們在這樣情況之下,強調說我們只維持憲法這樣架構,我想是有些自以為的,這樣的發展對台灣並不是一個有幫助的......
張:黃老師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在台大法律學院,我們都覺得,憲法老師可以教國際人權法,或者更應該教國際人權法,也要把國際人權的脈絡帶進來。我們裡面不只是我,像我們黃昭元教授,本來教憲法,也教公法,也教國際人權法。所以,你講這個方向完全是正確的,但我想在國內要克服還需要一段時間,當我剛開始在教學的時候,也很多人會比較傳統的問說,妳教憲法怎麼教國際人權法,因為他覺得這是兩個東西,憲法歸憲法,國際人權法歸國際人權法。
黃:在美國法學院幾乎都是跨的。
張:對,尤其現在越來越多,他們甚至會覺得你在談憲法或比較憲法你要比較瞭解歐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體制,這是很不一樣的發展。
黃:是,那你看我們還有待努力。
張:可能還需要努力。他們背後還有一個原因,過去我們威權時代很多人權論述不夠,後來司法院大法官透過憲法 解釋有一些發揮功能,那有時候很弔詭就是它可以有一些發揮功能,好像讓人覺得說好像從憲法可以補充,你後來看到其實還是不夠的,居住權、居住自由很多,那大法官對這些也還比較保守,所以我當然是覺得說這滙流的論述,對台灣整個人權的深化跟成熟是非常重要的。
黃:那你該多寫幾篇文章。我當然不需要跟你說,哪些憲法學者都對國際人權法都不怎麼願意去討論。我們法學院對我們人權研究中心,是想這個是法外之地,不能成什麼氣候的,看來還有待努力。另外最近,課綱微調的討論,也在很多人看法怎麼一下子就跟憲法有了關係。他們就說我們這個課綱的微調,是遵守憲法的,他們這樣的談憲法,我們剛剛說在台灣怎麼討論國際人權法,再來看看我們在台灣怎麼討論憲法,我也覺得有些很奇特的,這個課綱討論怎麼一下子就說我這樣的微調,是遵守憲法的,你這樣微調是不遵守憲法,你覺得這樣的討論是?
張:我覺得這樣的討論是讓人遺憾啦,而且他在講遵守不遵守憲法,他談的並不是憲法裡頭思想自由,然後,教學的這些研究自由,他談的是所謂憲法的國土啊領土啊或者是那個法統。這些其實不是憲法核心的部份,憲法最重要的還是這些思想自由、這些學習的權利。所以,我是覺得蠻遺憾的,台灣民主轉型到現在,我們還是把法律或規範工具化,嚴格來講課綱如果真的要調,台灣現在做為整個世界村,國際覺得我們對於、包括我們在上人權法的時候學生對於聯合國體系,對於這些聯合國相關的人權公約,其實瞭解非常少(黃:非常少、非常少),幾乎沒有,甚至尤其是法律人,他會思考到他將來除了台灣的這個法律的需求之外,還有哪些、這個世界很廣闊的法律需求,其實更少。所以,如果課綱要微調,應該要看看我們課綱有沒有遵守國際人權法,對不對,對這些思想自由,對絕對不能受酷刑的權利,你如果談,體罰就是一種酷刑,如果我們在課綱裡頭有這些,老師們在教學現場當然不可能用這種違反學生心理、身體、其他自由的權利的方式來教學。所以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課綱微調爭議,正反應出了我們現在還是一種對法律工具化,只用規範你覺得好用的部份,(黃:對。)該用的東西、人權思想都沒有被包括。
黃:而且,就表現得該怎麼說,並不願意去做功課,完全不做功課,就這樣引了,也是很草率的。你看,怎樣才可能把這樣的情形比較改變過來呢?有什麼想法嗎?
張:我在想過去這十幾年來,我們有些進步有限的地方,但大方向的進步還是在。例如,像我剛剛講,在我當學生的時代,除了必修的國際公法兩學分之外,沒有其他國際法的師資。現在,即使在台大法律學院,我們盡量的不斷在改革這事情,我們既有的師資要把國際人權法的課開出來,我們有訪問教授,國外的訪問教授我們也盡量邀請他們來開國際人權法、歐洲人權法上課,所以我覺得人權的教學,人權的理念散播,是很根本性的。像我常常在上人權法課的時候,我每次都會做這個測試,我剛剛有講到不受刑求的權利,那我就會跟同學說,你們知道不受酷刑的權利其實包含,按照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是不能受體罰,那體罰包含心理的跟身體的,然後我就會問全班同學說,你們有哪些同學到目前為只從來沒有受過任何的體罰?抱歉我必須要講,真的很令人難過,即便是我現在教的已經是1990年代出生以後,還是每次在我課堂上,舉手他沒有受過任何體罰的,大部分是外籍生,就是國外來台灣交換的學生,偶爾有一兩位大陸同學,他們可能因為一胎化。然後,但絕大多數台灣同學,還是各式各樣的體罰,甚至身體的體罰,而不是我說有沒有從小到大只有老師說你站到旁邊去冷靜一下,他們無法想像說老師請你去旁邊冷靜一下就已經是某種程度的酷刑了。所以我想路還很長,但那個方向我們已經看到了,所以黃老師你剛剛提到人權中心不重要、邊緣化,我想它是非常重要的,應該跟法學是一個核心、相互幫忙的資產。
黃:我不是說我們邊緣化,我是說我們法學院並不那麼重視人權中心,有時候我們的學生就人權學程的學生去找我們法學院,東吳法學院教授談話,都被受到質疑說你們幹嘛修人權課程。再問,妳對台灣憲法的研究跟教學妳做怎樣的評價?
張:台灣憲法的研究跟教學,我覺得相較於我在當學生的那個年代,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太多比如說當時憲法解釋、司法院大法官,還沒有發揮太多功能,所以能談的本土的、重要的憲法案例,然後包含人權這些議題還很少。現在當然大法官已經做了729號解釋,然後很多人權的增補,很多人權的憲法體制,所以整個憲法的教學跟研究,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進步。但進步的同時,還有一些可以再強化的地方,比如說這進步的同時,很多時候台灣的憲法學界,都覺得這些憲法的進一步,是受到外國法的影響,所以它可能、尤其我們大法官解釋裡頭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它可能學德國憲法、學日本憲法、學美國憲法,跟台灣法學院留學外國的背景也有關係。所以常常很多的憲法解釋跟憲法教學跟研究,還是以外國憲法或解釋,為主要範本跟參考,比較不能夠一看到本土,二看到國際,它比較不能夠看到說其實在台灣內部已經有很多新的人權論述、人權團體,人權需要。再來它比較不能夠看到國際,我剛剛講其實很多國家,國際人權法對憲法是一個很重要的補充;國際人權法、國際人權機制跟憲法也有很多互動關係,尤其是那些可以參與國際人權申訴機制的,像韓國,它的憲法法院決定不會是FINAL,因為它還會受到國際人權機制,像人權事務委員會,因為它允許韓國國民對它去申訴,所以像Jehovah's Witnesses,耶和華見證人的替代役問題,憲法法院說,強制他們當兵是合憲的,國際人權事務委員會就說是違憲的。那所以,所以很多國家它憲法必定要跟國際人權法討論,要磨合要匯流。這件事情在台灣還沒有發生,所以我會覺得有進步,但是還有可以填補的很大的感覺。
黃:我想這個在國際社會的這部份,情況是非常明確的,我們尤其不怎麼關心不怎麼瞭解的,在是在台灣內部有什麼新發展、新契機,我想,這部份實在是我們應該非常注意的,而且應該去鼓勵的,在法學院...
張: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像立法院上一個會期,去年,在暑假的時候很無預警地通過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的施行法,那,顯然有一些立法者,加上我們很多的人權團體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外面去參加這些公約,但這些公約可以透過兩公約、CEDAW施行法,內國法化來實踐它。但是很令人慚愧的是,這是很多法律學院的老師或憲法的教學研究者並不知道身心障礙者公約,是21世紀通過的公約,它很重要的內涵是什麼,然後所以反過來,很多法學院的學生,更不用講,他根本沒聽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其實國內的有一些人權的區塊,有一些人權團體或有部份的社會或政治的精英他跑得比較快,有一些發展,跟國際的人權趨勢有一些連結。但我們中間這個區塊的傳統的法律教學、傳統法律研究還沒追上來,像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例子,反過來它現在內國法化了,所以很多人就要去研究說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到底有哪些,兒童人權公約裡頭規定的是什麼,我們要如何來實踐它。
黃:妳看是不是就...
張:我們先到這裡好了。
專訪張文貞教授(二)
黃:大家好我叫黃默,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我們很幸運地再度邀請到台灣大學法學院張文貞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在六月間已經訪問她一次了,但我們有很多問題想再來請教她。上一次我們也稍微提到憲法跟課綱微調的這件事情,當時我們沒有做很多討論,當時我的想法是憲法我們怎麼樣去引用憲法,當時,也沒想到說會有這麼多的爭論,學生抱怨教育部,教育部又起訴幾個中學生,所以,對這個課綱爭論,妳有什麼新的看法或者進一步的看法?
張:謝謝黃老師,我還是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多談人權這方面議題,課綱這方面問題這陣子以來談得非常多,但我想提出一個到目前為止沒有人重視的面向。這次受到爭議的是高中的課綱,這課綱適用的是所有18歲以下的高中生。當然我們整個基礎的教育還包括國小國中,這是高中,基礎教育最後的階段,18歲以下的高中生其實就是兒童,他是《兒童權利公約》最需要去保障的主體。去年的這個時候,去年暑假,雖然我們的立法院沒有批准《兒童權利公約》,但以施行法的方式,將《兒童權利公約》納入成為我國內國法的一部分,今年也正式生效了。那這個《兒童權利公約》,保障了18歲以下兒童表意的自由,所有成人受保障的政治權利,在這個《兒童權利公約》裡頭,都對兒童予以保障。那所以事實上,學生對於他所受教育的內容,是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在《兒童權利公約》裡頭,他表達意見的自由,他陳述意見的自由,在好幾個條文裡頭都保障得很詳細。那我想高中生對他所要接受的教材,他有意見,他需要表達,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這個課綱要施行之前,大部分很多媒體討論到的,正當程序、這個委員會裡頭要有比較多元的代表性,我都同意,可是還有一個在台灣因為人權思考比較少而沒有被納進來的面向是:這些受教育的主體,這些18歲以下兒童,他對於他所受教育的內容,他們也有表達意見的機會,所以將來這些委員會也該有學生的代表,這面向是比較少被提到的。
黃:我想這沒錯,我也沒有讀到這方面的討論,看來妳應該又寫一篇文章了。我剛剛提到憲法課綱,是看到一個情況有些弔詭,比如說我們有些學者看來有幾位是參加課綱審評的,他們就說,憲法我們怎麼說,所以我們就該怎麼樣來訂課綱,我是有點遲疑。但是呢,從另一方面,我們在社會上,多年來又有一個論點,就是這件事情是無法可依,就是說沒有法律管這件事情。我多年來也非常納悶,無法可依?這指的是什麼?法律是來規範我們生活的,有很多新的問題出現了,在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新的問題出現了,不可能每個生活細節都有法律來規範,所以我們說無法可依,看來一個程度就是很……看來我們政府部門是十分不負責任的一個……所以我們一方面有些人說,這個憲法已經規範好了,我們就這樣訂在課綱,另一方面就是說,我們無法可依。妳對這樣弔詭的情況做什麼看法?
張:黃老師,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兩個方向來看。第一個是到底課綱這個爭議,對於支持新課綱的人來說,我是依照憲法,這個談法事實上是蠻有問題的,第一個是說,當代憲法最重要的核心是在保障人權,所以,而且是政府的施政不能夠去侵害人權,而不是說人民的行為,要合乎憲法限制性的規範,這是兩個問題,這完全是兩件事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人民的思想自由、接受教育的自由、參與教育形成的自由,政府一旦通過課綱的方式去統一化的時候,這統一化的過程應該要接受憲法的檢驗,而不是擬定的內容合乎憲法就好了。擬定的內容是不是真的合乎憲法,這件事情即便在中華民國憲法文字上的規定,也是有爭議的,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很清楚地,制憲當時,就已經陷入了戰後、國共對立等等,雖然好不容易有一個參與的,大家都參與、各政黨都參與的這個制憲會議,但後來共產黨還是很可惜的退出了。所以憲法的條文裡頭很清楚有些妥協,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領土疆域這一塊,就很清楚規定了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個固有的疆域範圍,他去解決了那個,因為過去的草案都是明定的,明定中華民國憲法是哪些哪些地方,還有一個草案並不包含臺灣省,因為當時臺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範圍內,所以制憲當時,明顯去談了固有疆域。後來大法官在民主轉型之後,被立法院聲請了解釋我們的疆域到底在哪裡,大法官也很清楚的說,這是固有,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我不能解釋。所以很顯然,面對我們所處的台灣,或者中華民國的歷史政治的現實,連憲法都沒有辦法、他用固有疆域的方式去迴避了很具爭議性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我想各界不能夠用自己所定義的疆域,或自己的意識型態去說我這個是符合憲法的,因為憲法沒有明定,所以我覺得用這個論點拿著憲法的劍,然後去說他所認定的疆域、他所認定的歷史,就是別人該合乎憲法的疆域跟歷史,這是很讓人遺憾的事情,因為他並沒有清楚看到中華民國的憲法條文裡頭並沒有去說涵蓋哪些地方,而且這在當時就很清楚是一個政治妥協,就是固有。因為連在制憲當時就沒有辦法確定,因為很多地方戰亂,我覺得很可惜。另外一個、第二個層次,就是我剛剛提到,第二個層次,課綱這個問題會不會是無法可依呢?不會,在我的這個法治社會裡頭,剛剛講過了,本來人民就有表意的自由,他有意見對於他所必須接受的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因為那對他的思想、他的人格的形成過程中,一個統一的要求的義務國民教育,對於這樣內容,其實18歲以下兒童或者他的父母,都有一個人權,是必須要能夠參與形成表達不同意見,這其實是用我們國內對於教育的意見性表達人權不夠清楚,所以一直不在意這個部分。其實回過頭來我們有高級中學法,我們有這些國民教育法,回過頭來我們應該是要去檢視這些法律所形塑的國民義務教育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不當的侵害了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表意的自由,然後這個過程當中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有沒有讓這些要接受義務教育的主體,現在已經納入了《兒童權利公約》保障範圍的18歲以下兒童有完整表達意見的權利。所以由這個角度來講,這樣的法或者權利的保障,是非常多的,我們絕對都有,所以不會是一個無法可依的情況,只是說談這個話的人,他想依的法,是他心中的什麼法。
黃:我剛才談,無法可依,並沒有想到這個,課綱。我想到就很多食安的問題啊、環境的問題啊,政府部門都說無法可依,都管不了,我就多年來在想這是怎樣的一件事。看來你們憲法學者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做,很多概念要去幫我們大家釐清,我們談到教育都是傳統要去管小孩嘛,所以受教育的這些年輕人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啊,他們對課綱提出什麼看法,我們都是、都很難接受。像這次爭論,都說是有政治力量在背後掌控等等,所以看來還有很多很多問題需要一步一步去釐清的,所以你們憲法學者是任重道遠、任重道遠。
張:不只憲法,我想人權學者也都是,憲法人權是不可分的,雖然也慚愧,但我確實也覺得,因為當時發生的時候,我剛好從國外回來,看到很多人其實這些高中生,是這麼大的一個孩子了,他們當然是權利的主體,然後他們說他們沒有對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有批判的權利,這是讓人覺得很遺憾的。
黃:我們大家都說他們是小孩子,他們不了解,他們怎麼能發表意見?這是很基本的對台灣社會的動向,往哪裡去,是很基本的問題。假如我們這樣想,那看來臺灣社會下一步就很難能展開出來。
張:而且批評這些小孩的很多立法委員,他可能忘了,他自己去年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的施行法,裡頭明白保障了這些他現在所謂的不懂事的高中生的表達意見的自由,甚至他思想的自由,他跟成人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模一樣的權利。
黃:是,那好了,我們就不談這些立法委員了,多年來你都關注好些議題,我稍微看了一下,比如說環保,你關心寫過很多文章;專注死刑的問題,也盡了很大力量,我記得上次我們請了好多外國學者來,在台大開會。另外是你對於兩公約的、我們要提國家報告的時候你參與很多,所以我也想聽聽你來談談你參與這些公共議題的經驗與觀念怎麼樣。
張:確實沒有錯,就整體而言,上次談到的,對憲法跟人權尤其在台灣面對憲法跟國際人權的發展,必須要有一個整合,這樣的一個最根本的發展趨勢,我是最關心的,所以整體而言我的整個研究、教學甚至努力的方向都最在意這個事情,(黃:圍繞著這個事情)對,圍繞著這個事情,但是有一些子議題確實是我從過去不管是生命故事的角度出發,或者對特定議題的關心,我很在意的,這是黃老師剛剛提到的環境、死刑、然後公約,公約也是跟剛剛那個有關,我很在意的,因為台灣這麼的偏離國際社會,怎麼樣在台灣自己的發展當中,怎麼讓國際社會的整個發展來帶動台灣的發展,這是我很在意的。我在參與環境跟死刑這兩塊議題裡頭,我的感覺是,這兩塊議題都是在我自己還小的時候,高中的時候甚至還沒有進大學,懵懵懂懂,就還在啟蒙的時候,就受到很大的影響。死刑的議題是原住民青年湯英伸,湯英伸的案子發生的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在我高中的時候,當時還沒有解嚴,台灣解嚴是1976年,那我1975年進高中,1977年進……1985年進高中,1988年進大學,所以剛好在那個轉型期。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湯英伸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一個原住民青年他下了山,工作到處碰壁,最後在一個洗衣店,身分證又被收走,在一個很辛苦勞動的過程中,當然最後殺死了雇用他的一家人。全台灣當然很震驚,有些人認為應該要處死刑,有些人就會看……對我來講震撼比較大的是,在我們那個高中的時代很少同學知道這個事情,當時人間月刊才剛……(黃:成立出版)出版沒有多久,我們幾乎是要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吧,才能去找到一個,幾個當時比較有人權意識或政治意識,或單純只是關心社會的一些同學,私底下傳才看得到這些東西。所以這算是我對……包括說前陣子在參與那個前許玉秀大法官辦的第二屆模擬憲法法庭,同時其中一位模擬大法官張娟芬作家,她是我的高中同學,我們其實在那個時代都受到湯英伸的案子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今年也很高興,後來這個模擬法庭的案子就是以湯英伸的案子取了個假名叫做湯申案,我們兩個都覺得很有意義的是,我們當時都受到這個案子的影響,現在一起坐在這個、來看這個案子。這個是死刑的議題,其實死刑的議題在台灣社會,甚至在民主轉型之前,就一直有重大的事件,有很多很多的討論。但相較於這二、三十年在其他國家有很多重大的進展或反省,即便包括美國,它透過很多案子不斷去反省,對於身心障礙者,對於兒童,對於各種狀態,儘管它沒有完全廢除死刑,但有很多反省檢討正當程序、死刑的方式。但是,在這二三十年間,在台灣在這塊議題,我自己的感覺,從我高中到我後來回來教書,到兩公約通過,在整個社會跟政治結論上沒有太大進展,當然這樣講不公平,(黃:對,民間)民間,民間是非常的努力,所以包括說我在高中時候人間那個專輯,律師、NGO、這整個過程當中包括廢死聯盟包括東吳人權中心很多的參與,民間很努力,正因為民間一直不斷的努力而且是在轉型前就很努力,那個落差,是讓我每次廢死聯盟的欣怡,只要找我要做什麼的時候,儘管我還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就會說這是一個道德使命感的事情一定要做,這是死刑的議題。我也一直在思考,所以當然我後來採取的一個策略,是有兩公約那樣的一個momentum,那我就覺得說是不是至少,讓國際人權公約裡頭的,許多不管是正當程序也好、對於被告的保障也好、對於什麼樣最嚴厲的罪行才可以處以死刑,很多的討論,至少它能夠進到台灣來,而且剛好政府部門也讓兩公約內國法化,所以這樣能夠去帶動深化對於死刑這方面的討論,這是一個死刑方面的議題,我的算是說心路歷程。
黃:你做得非常多,看來我們傳統的想法對於死刑都不願意放、不願意開放去想。我稍微想了一下,從這個批准兩公約以後,看來我想,政府最不願意做什麼妥協呢?一個就是廢除死刑,另一個我看來就是去設一個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對這兩個議題他們是堅守陣地,一切都不放棄的樣子,是嗎?是。我想,環保呢?環保你怎麼看呢?
張:環境的議題也一樣,我自己的爸爸媽媽是彰化人,我爸爸那邊是在鹿港旁邊的福興鄉,所以,福興鄉是一個非常貧窮的鄉鎮,爺爺的田就真的在田中,很貧瘠,田中。外公外婆家在王功,現在有所謂王功漁火節,但是在當年,現在其實也還是一樣,如果有機會去王功漁村看,真的是一個貧瘠的地方。但是在我小時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雖然很美麗的農村漁村,但慢慢開始蓋起工廠,慢慢有了污染,生活條件非常地不好,所以我自己雖然是在台北出生,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是兩個家族最小的小孩,很清楚的顯示了台灣人由南向北遷徙,因為他就會被期待你應該要去台北奮鬥,所以爸爸媽媽結婚之後就到台北來,我是在台北出生,甚至我講話的口音常常被認為我不會講台語,確實我也講得不好。我的這個過程正好反映了台灣在戒嚴、轉型的這整個過程當中以北部發展為重心,中南部尤其是農村漁村幾乎沒有發展的機會。母語當然更不用講,到台北來就是要把書念好要把國語講好,我是很典型的這個。但是讓我關心環境的議題,也是一樣,就像剛剛講到我高中1980年代的時候,其實我們常常今天在講貧富差距,但在當時我們常常講「臺灣錢,淹腳目」,股市是上萬點,很多人很有錢的時候,中南部貧瘠的地方環境的問題、污染的問題,在1980年代我想黃老師應該記憶猶新,就顯現出來了。當時有很多鎘的污染、農田的污染、漁村的污染的抗爭,雖然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沒有出現在台北的電視,但那些抗爭是很激烈的,因為是農民漁民的關係,他完全沒有機會。我因為這樣背景的關係,雖然我看起來像是台北小孩,不知道農村漁村長什麼樣子,可是我高中考上大學那年我是回去王功,住在我姨丈家,坐著牛車下去撿蚵。今天是很流行所謂休閒漁村的活動,當年我是暑假的時候回去跟著做這些事情。那,所以我關心環境的議題,我剛剛講說我關心很多議題是跟生命故事有關係是這樣子,到了我大學時候也受到我自己碩士班老師的啟蒙,葉俊榮老師,他自己是做環境法。環境法也有一個很大特色是,葉老師也不是只談環境法律的規定,他真的會在課堂上帶我們看到許多漂亮的土地,但是抗爭的運動。在那些抗爭的人的臉上,我看到自己的叔叔伯伯、舅舅阿姨,包括前陣子中科三期四期,當時也很慚愧,回來忙於學術的研究。當時看到中科四期的判決書的時候,芳苑村,所有人的姓都跟我姨丈同姓,就感受到那樣,像死刑議題一樣,我感覺到台灣土地的議題,對農村、漁村的許多好幾層的壓迫。儘管經過二三十年,我們環境法規有很大的進展,但是,這些議題其實還是存在一個很大的結構上面的問題跟反差,所以講起來也要很慚愧,我也覺得進展,像我剛才講的死刑的議題,台灣社會經過這二三十年從轉型到民主到現在,對生命權對正當程序的認知不夠,同樣的我們對於環境的認知,我覺得也非常不夠,這樣講也不太公平,還是有很多進展,有很多環境團體、環境律師,我們有很多的環境法規。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我常常上課的時候驚訝於同學沒有去過農村、漁村,沒有去看到那個壓迫,那個人權侵害是怎樣真實的存在,這是環境的議題。
黃:你已經做了很多,這幾年來我稍微觀察不管在學術上在理論上,在實踐方面你已經做了很多。我很同意你的看法,看來我們關懷的議題,跟我們生命或多或少,只要我們去想的話,都有些關係,不然就不可能有這樣的關懷。你希望引進國際人權法跟憲法的互動,還是關連,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跟現實的生活希望能做一個聯繫,我想這是非常有意義。而且在當前台灣社會,我個人看法是最需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我想或多或少我對有些學法律的朋友有些批評、有些微詞,就是說他們一方面不問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對很現實的議題他們看來也不是那麼關心,所以我就想那你們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這樣說也有點不公平……
張:不會,黃老師你的觀察是很切中要害的,其實國內的法學的教學或課程,是這幾年來才很重視實務課程。像我剛才說的我很驚訝於同學從來沒去過現場、或者農村漁村,甚至山上。這幾年來,比如說我前陣子在士林文林苑王家,很多同學可能在媒體上看到這個事情,讀到一些討論,但是我那時跟一位外籍教授一起在上這個課程,士林那麼近,那我們、但我也很驚訝很多同學都不知道士林王家到底在哪裡,我們甚至有個,說起來真的是慚愧,field trip,一般field trip是比較遠的,但我們field trip就在台北,搭個捷運就可以到士林王家,同學真的看到了那個地方才會對這些權利有感覺,這些事情我們慢慢在做,但黃老師你的觀察是很切身的,也是法律的教學或者實踐需要改變的。另一個是很重視內國法不重視國際人權法,我剛剛講到就是模擬憲法法庭死刑那個例子,國際人權法當然不是萬靈丹,也不是最棒的人權標準,就像《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他沒有直接的廢除死刑,很多人爭議說他其實還是應該往廢除死刑的方向。但是我一直希望他能夠引進來討論的是,包括五月我們那個模擬憲法法庭,九位民間大家遴選出來的大法官,每個人來的立場都不同,到最後,其實還是有所謂的完全廢死派,認為死刑絕對違憲,或認為死刑不違憲,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場。但我自己感覺amazing的是,公政公約第六條、第十四條許多的規定的關係,所以我們最後其實我在最近全國律師七月號寫了一個,我們很amazing發展出交疊的共識,多層次,其實我們只有五票認為死刑是違憲的。所以、但是我們有七票,因為總共有九位大法官,我們有七票,認為刑法271條,殺人者處死的規定違憲,因為它沒有規定情狀,沒有看到哪些情狀才是所謂公約第六條最嚴重的罪行,而且這論點從我們本來認為他是認為死刑是合憲的同僚,最後經過很多討論的轉變。我們九位,所有人都覺得現在台灣在科處死刑、完成死刑的方式,完全不合於公約所要求的正當程序跟人權的相關規定。所以,公政公約的國際人權標準不是最高標準,但是即使是引入這個討論,我自己至少是覺得說,讓我們當時立場不同的九位,而且我們在討論過程發現說,我們真的很努力不斷地討論。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場,離開了以後,也許對死刑絕對性還是有各自的立場,但是能去區分程序、實質、最嚴厲罪行這很多很多討論,其實是帶進國際人權論述,去活化、豐富化這些論述的優點。因為國際人權法本來就是讓立場完全不同的各國能夠有一個共識在那裡,它不是高標也不是低標,它的豐富多層次,剛好可以讓對很多問題窄化或者沒辦法豐富討論的台灣,有一些可能性。這個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說,引入國際人權法論述,最讓我覺得amazing或者最棒的功能,我不是說我們把國際人權法放得很高,放得⋯⋯我們去跟他接軌,不是,而是一個社會封閉久了,它有很多論述沒有辦法豐富、多層次,沒有辦法真的放開來討論。國際人權法剛好有這優點,它裡頭是很多元、很多衝突的,那它進來讓台灣社會不同立場、對立論述有了新的空間,這是我的想法。
黃: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想有些時候我們也看到這樣的一個批評就是說,我們比較同情,或者希望引進國際人權法的,就被批評說是迷信國際人權法,把國際人權法看做聖經之類的,我想不是這樣的事情,但是怎麼樣來跟我們的一些同儕、還是跟台灣的社會說明這件事情,看來並不是很容易、並不很容易,我的經驗並不容易。
張:尤其國際人權……尤其台灣的論述,黃老師剛剛講,去提倡國際人權法被誤以為是西化主義者、高標論,其實不是。我暑假剛好用這段時間整理了一下家裡的書啊,找到了我1998年在耶魯法學院上課的時候,國際人權法的seminar,Harold Koh教授上的教材,我發現我自己的筆記,這樣一行一行的,那時候回去看二十幾年的東西蠻好玩的。其實國際人權法的東西,黃老師也知道,裡頭有一個,它在整個形塑過程中,要去整合非常多多元不同的觀點,它的這個過程裡頭這個內容,最值得我們treasure最值得珍惜的,其實是它在過程當中,最後形塑所謂這個公約,過程當中就有很多論辯,很多過程,很多價值,最後出來的可能還是包含很多多元解釋的可能性。正是這個東西,很需要跟我們這個單一、動不動就對立、意識型態化的台灣社會來討論。所以我自己……但這個事情真的需要多努力沒有錯,做國際人權法真的會被誤解,以為說你這樣一個研究取向,跟標榜美國化,因為在法律老師提到的,法律經常以過去一個問題是說,就是引用特定的外國,總覺得美國好、德國好、日本好,於是就陷入了一個人家好的爭執,而沒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多元的討論空間,可是當國際人權法加進來之後,好像就變成另一種誤解,變成國際好、歐盟好,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
黃:那怎麼辦呢,有這麼多誤解,有什麼好的辦法?
張:我覺得人權中心在做的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
黃:我們沒有做什麼事情啊。
張:還有就是剛剛黃老師講的就是,我們要繼續努力讓國際人權的論述跟對話是一個提倡多元跟不斷地把這些價值衝突,納進一個法的討論體系,這樣的一個本質內容,透過我們教學、透過我們研究讓它更清楚,而不是好像拿著一個尚方寶劍,這國際人權法你要接軌它你要遵從它,而是這些國際人權法,這些國際論述,它重要的是它在於這個過程。台灣沒有機會參與,不知道過程當中這公約內容是什麼,它其實有很多論辯、很多討論、很多價值衝突在這裡頭都經過很多討論。我覺得多參與也許是一個努力的方向,現在其實有很多國際組織對台灣學生學者開放,所以如果我們有更多參與跟了解這些過程,那他回來參與台灣這些論述的時候也許會更容易一點。
黃:我想你說得非常好,一下子也不是有、立即就有什麼……
張:立即的診斷處方可能沒有。
黃:你對今後,能這樣說,今後幾年,台灣的人權狀況還是對台灣人權保障、人權理念的傳播,你的看法怎麼樣?想說你是比較悲觀還是樂觀的還是怎樣?
張:我是樂觀的耶,我從今年暑假,這麼多高中的同學,很勇敢很積極地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的內容、課綱的程序,黑箱的問題,可以這麼勇敢的上街頭,主張發聲,我很清楚看到台灣看到在整個民主轉型,人權法治教育的深化上已經有了一個全新的generation。我覺得這個generation是一個不同於過去我們連看著湯英伸那案子,都還要私底下同學在抽屜底下傳人間雜誌,是非常不一樣。它是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在一個知道人權是什麼,有權利意識,然後在一個民主法治社會長大的新的一代。所以我認為台灣將來對於這些人權跟權利意識的爭取,只會越來越往這個方向去,任何政治勢力,任何倒退勢力都擋不住。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些法治、人權教育工作者,我們這些在學校的老師,或者社會上的知識份子,怎樣很珍惜新的一代,怎樣在我們教學在我們研究過程當中,能將這樣的東西,第一個是去肯認、昂揚它,這新一代人權意識發展,對台灣整個社會發展是正面的,事實上對全球來講都是正面的。我們怎樣在教育跟研究工作當中,就像我剛剛講的,當時很慚愧沒能很快寫,再來一定要寫高中課綱、學生這些爭取其實是就是在實踐《兒童權利公約》。我樂觀的原因,還不只是台灣的新一代,我覺得整個亞洲、東亞的新一代都已經成形,其實在台灣發生這些課綱抗爭的同時,日本,日本其實有很多高中跟大學生上街頭,為了安倍政府通過人家所謂的security law,這些國家安全法,擔心日本新一代的戰爭的問題,然後修憲的問題。我其實我剛好七月初的時候參與國際會議,跟很多日本學者很關心,甚至我也做了一個國際的連署,是支持日本這些青年學生,上街頭表達意見。日本其實1960年代之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年輕世代對於不關他自己、但是公共的議題發聲,而且到現在他們每個禮拜五都還上街頭表達意見,我所知道他們跟香港學生的雨傘運動、或者台灣太陽花運動,都有一些在網路的學習。我覺得這些都代表整個亞洲社會經過過去這二三十年法治化、人權發展,新一代已經形成了。其實我是因為新一代形成的這個發展趨勢而感到樂觀,但當然政府或者老一輩很多觀念、社會的改革也許還沒跟上來,這裡我倒不致於悲觀,但是這是需要努力的部份。可是我相信再過二、三十年,不只台灣社會會不一樣,我相信整個亞洲的社會,都會不一樣,這個是我至少從這個暑假,雖然想到反課綱學生的一些遭遇,甚至自殺的同學,感到傷心跟不捨,可是我們從當中也看到力量,看到我們自己作為在大學教書的老師更該做的許多事情。
黃:這我都同意,我想只要從台灣發展來看,這樣一個新的世代、新的思維、新的價值觀,看來是勢不可當,我不了解你怎麼看,假如我們把我們討論再稍微延伸一下,立即就帶出來,台灣外部的影響又可能怎麼樣。我不……你看看是不是對這個問題做個回應,或者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子再回來談?你怎麼看?
張:我直接把那個外部的那個部分,我剛剛已經談到說,日本在這個暑假,看起來雖然有一些政府看起來比較保守或者人權上,看起來比較讓人憂慮的國家安全法,但他們年輕的一代,完全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年紀……高中、大學生他因為他新的一代養成人權的意識,他上街頭,所以整個亞洲區域發展對台灣是重要的。很多人往往只從、這也是傳統……。人權中心在東吳政治系的合作很密切,但傳統上我們常常只從區域的和平安全或政治角度來看問題,卻很少從區域的人權發展,法治的角度去看問題。所以我自己覺得,雖然現在國際上對區域跟台灣,雖然也有所謂樂觀悲觀,那悲觀就是認為說好像整個亞洲,中國的保守政治勢力,為了經濟發展正在興起;日本也有一個保守政治勢力,韓國這兩天兩韓對立,所以使得亞洲區域安全形成一個比較緊張的態勢,政治發展也是比較倒退的,因此也擔心它的和平。樂觀的,樂觀也好幾年了,就是所謂東亞崛起論,經濟發展,亞洲的經濟、東南亞的經濟發展,但我不從這兩個觀點看問題,因為其實政治跟經濟的發展,都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會影響到經濟弱勢的人權的傾軋,環境土地正義。政治發展不用講,在大陸在中國對於維權律師、人權工作者的侵害是更嚴重的。在日本,連青少年都會起來為國家安全法裡頭侵犯的人權,可能引發的東亞衝突感到憂慮,這兩個都不管,比較讓我能夠正向看待的是,過去這幾年來這個區域裡頭的人權組織的連結,我剛剛講的年輕世代的人權意識的高漲,到一個程度是他會起身行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台灣的太陽花、今年的課綱,日本,這些大學生、高中生的反對國安法運動,你都看到是一個年輕的區域的人權世代形成,不只是人權意識,他已經從conscious到action,這個是讓我覺得東亞人權的人權運動,東亞人權的合作,才是對東亞和平最重要穩固的基石,我們如果沒有一個人權的世代,能在每個社會深耕,我們就很難奢望21世紀的東亞和平。黃老師跟我都是,我們還記得20世紀的東亞是怎樣獨裁者在每一個地方,社會的人權意識是怎樣剛長出幼苗就被壓抑。我也是小時候必須到地下室偷偷看我爸爸藏在地下室裡頭的自由中國。到現在,這個人權意識已經形成,這些年輕世代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要談,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我也覺得有很多NGO在做了,是我們本土的人權運動要跟區域的人權運動,區域人權發展緊密連結,我們要覺得中國人權律師、中國人權發展、日本人權發展、韓國人權發展,跟台灣的人權發展是一樣重要的,我們不是只關心台灣人權,其他地方,其他我們的鄰居,有好的人權保障,才會有區域的和平,我的感覺是這樣。
黃:我非常同意,我們是不是已經談了一個小時了?我們是不是就在這裡停下來,我們以後再邀你來受訪,我還有很多問題想問你,謝謝張文貞教授。
張:謝謝黃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